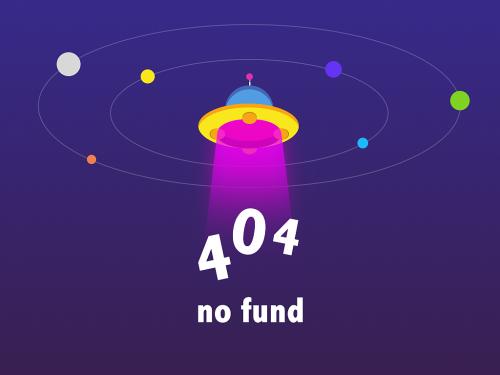2019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以下简称“《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以下简称“《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1]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2]规定的行政协议案件作出司法解释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行政协议案件又专门做了规定。虽然《行政协议案件规定》还未正式施行[3],但因该规定第二条将符合规定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4]纳入行政协议案件的受理范围,对政府和合作资本合作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业界对该规定持悲观态度的居多,认为规定的出台将严重影响社会资本在ppp协议中寻求救济的能力。为全面理解《行政协议案件规定》和为积极应对ppp协议争议解决作准备,本文将在总体评述《行政协议案件规定》对ppp协议影响的基础上,论述如何识别ppp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以及依据《行政协议案件规定》对ppp协议的社会资本寻求救济的影响。
一、《行政协议案件规定》增加了社会资本对ppp协议争议解决的难度吗?
笔者认为《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的出台基本搭建了解决ppp协议争议的规范适用框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ppp协议争议的解决,能够较好地维护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但规定的出台也并未完全平息关于ppp协议争议解决方面的争议,因此不设前提的悲观或乐观地分析、评价《行政协议案件规定》对ppp协议的影响都有失偏颇。理由如下:
首先,《行政协议案件规定》并未将所有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纳入行政协议案件受理范围。规定在列举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作为行政协议时特别强调了“符合规定”的前提条件,对比不含前提条件的“特许经营协议”的表述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并非所有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均属于行政协议,发生争议时即均应作为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处理,实践过程中仍需结合项目实际情况予以分析、判断。
其次,《行政协议案件规定》以一般性陈述和正面有限列举的方式试图阐述行政协议的内涵,为确定行政协议案件的范围指明方向,但分析相关条文的内容可知,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特许经营协议等协议的内涵与外延尚不清晰的情况下,即使适用《行政协议案件规定》也无法直接得出ppp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的结论,也无法直接确定是否应按照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处理。[5]
最后,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相较于政府特许经营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发展周期较短,现阶段关于ppp协议争议解决的司法实践经验绝大部分为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争议的情况,而鲜有真正意义上的ppp协议的争议解决经验积累。在《行政协议案件规定》出台前,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已经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直接纳入了行政协议范畴,但司法实践中也并未依据特许经营协议的名称、类型直接认定相关争议为行政诉讼案件,而是依据行政协议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且在认定均为特许经营协议的基础上不同案件也依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6]因此,《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的出台,也并不意味着实务中即已认定ppp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并确定相关争议按照行政诉讼进行处理。具体的ppp协议发生争议时,是否属于行政协议争议并按照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处理,仍需结合项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综上所述,虽然《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的出台并未一劳永逸的解决ppp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范畴的争议,但实践中也不应“望文生义”的认定ppp协议均属于行政协议,发生争议时即按照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处理。《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的出台并未因此增加解决ppp协议纠纷的困难程度,社会资本应该在全面理解行政协议的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合理判断具体项目的ppp协议争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争议,选择恰当的争议解决方式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第一条规定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相较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十一条的规定,该条删除了“在法定职责范围内”的表述,即删除了行政协议中关于职责要素的规定。[7]针对行政协议的识别,理论上有单一标准和综合标准两种观点。
单一标准分为主体说、目的说、标的说和公权力行使说。主体说认为行政机关作为合同主体,包括行政机关的授权主体、委托主体,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签订的协议为行政协议。目的说认为基于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目标所签订的协议为行政协议。标的说认为协议中以行政法律法规为依据,包含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为行政协议。公权力行使说认为协议中具备公共权力的使用、公共任务和公共财物等因素的,即应认定为行政协议。[8]单一标准学说均侧重于行政协议的单一核心特征,显然以此标准判断是否属于行政协议不能满足实践需要。
相较于单一标准学说,基于行政协议概念,司法实践更倾向于综合标准学说,[9]即在认定是否属于行政协议时,应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要素:一是主体要素,即一方当事人必须为行政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委托的机构、授权的机构,除合同主体具备的形式要件外,还需进一步考察合同主体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协议受益主体、协议目的等因素。二是目的要素,即协议必须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目标,以此区别于行政机关基于自身需要通过采购方式签署的政府采购合同,进而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2014修正)》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对于行政协议识别、认定的影响。判断目的要素时,协议中是否约定或法律规范是否规定行政机关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可以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单方面作出变更、解除协议[10]的内容是一项重要参考标准,具备此类型内容的一般推定协议满足行政协议的目的要素。而且应予注意的是目的要素并不排除行政协议相对方实现私人利益和适度收益的私人目的。[11]三是内容要素,协议内容必须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即协议中是否包括民事主体无法自由行使、处分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包括行政机关基于法定职责所实施的行政职权。四是意思要素,即行政协议必须经行政机关及相对方协商一致,协商一致不仅包括事实层面的协商行为,也包括法律层面的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协议当事人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应当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不能处于“命令—服从”的隶属关系。[12]因行政协议具备“行政性”和“协议性”的复合属性,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协议中约定的“本着平等、自愿原则”、“ 经友好协商”等内容,即认定协议为非行政协议。[13]
针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的ppp协议,实践中也应按照上述综合标准学说确定的四个要素进行识别,协议识别时可以采用“先形式标准,后实质标准”的方式分两个步骤进行。[14]一是识别协议是否具备主体要素和意思要素,即ppp协议中的项目实施机构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授权、委托机构,且协议当事人缔结协议是否符合协商一致订立的要求,确认当事人之间是否处于“命令—服从”的隶属关系之中,排除《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第三条规定的两种类型的协议:(一)行政机关之间因公务协助等事由而订立的协议;(二)行政机关与其工作人员订立的劳动人事协议。二是识别协议中是否具备目的要素和内容要素,即协议中是否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单方变更、撤销协议的内容,如ppp协议中经常约定的行政机关的监督权、临时接管权。以及行政机关在协议的经营内容、范围、合作期限的确定、价格收费标准的确定、设备设施的归属与处置等方面体现了其特殊地位,[15]如收费公路、污水处理厂等经营性项目的收费行政许可等即体现了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行政许可的特殊地位。
当然,即使按照上述识别要素,要准确识别认定ppp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也并非易事。经案例研究发现,行政法官和民事法官在识别行政协议时,均不是只看协议名称,而是基本上都能按照前述综合标准学说对协议按照要素内容进行分析,但双方对分析协议的内容要素的权重认定上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双方在识别行政协议时存在实质分歧。[16]因此在处理具体ppp协议争议时,应结合法院司法实践经验,对协议内容进行深入的分析判断,以确定ppp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
三、按照行政诉讼模式处理ppp协议纠纷影响社会资本寻求救济的能力吗?
针对具体的ppp协议纠纷,若认定ppp协议属于行政协议的,则应按照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处理。
对ppp协议提起行政诉讼,并非使政府方处于更优于民事诉讼之处。虽然相比于民事诉讼法而言,《行政诉讼法》一般性地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17]此与民事诉讼法原则上由原告负举证责任不同。但在行政协议纠纷中,根据《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第十条规定,原告主张协议撤销、终止的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行政协议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对于自己具有法定职权、履行法定程序、履行相应法定职责以及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即使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按照民事诉讼处理亦应由行政机关举证证明已依法依约履行或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因此,政府在行政协议的行政诉讼中和相较于民事诉讼并无明显优势。
在《行政协议案件规定》出台前,部分司法实践认为,行政协议诉讼受理范围仅限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行政协议、行政机关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行政机关违法变更行政协议、行政机关违法解除行政协议等。[18]限制了相对方寻求救济的范围,但《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第九条[19]纠正了此类错误做法,扩大了行政协议诉讼中相对人可以主张的诉讼请求的类型,除《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的四项诉讼请求类型外,还包括协议订立时的缔约过失、协议成立与否、协议有效无效、撤销、解除协议、请求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承担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等类型的诉讼请求,[20]而且根据《行政协议案件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因此即使行政诉讼存在被告恒定原则的限制,即行政诉讼只可“民告官”,而不可能“官告民”,该原则也不影响作为ppp协议中的社会资本提起诉讼的请求范围。总体而言,因ppp协议社会资本可以针对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发生的纠纷提起行政诉讼,因此提起行政诉讼基本上不影响社会资本主张实体法方面的权益。但应予注意的是,与民事诉讼相比,若社会资本针对ppp协议纠纷提起行政诉讼,在以下几个方面仍需要高度关注:
一是行政诉讼中诉讼时效的不同。《行政协议案件规定》将行政协议案件中相对方主张权利的期限进行分类约定:若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若对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因此在社会资本对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主张权利的起诉期限为6个月,除《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应当延长或可申请延长的情形外,起诉期限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的规定,社会资本可主张权利的期限较民事诉讼更短,而且超过起诉期限而逾期起诉,法院不予受理,相对民事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更加严苛。
二是行政协议纠纷案件适用的规范类型更加广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法释[2009]14号)第五条规定:“行政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解释或者行政规章,可以直接引用。”对比民事案件法院引用规范文件的规定,行政案件所适用规范更多。以无效事由为例,除《行政协议案件规定》规定的适用民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外,因受制于依法行政原则的制约,行政协议特别强调行政机关是否具有法定职权、是否履行法定程序,对于没有法定职权、超越法定职权、没有履行法定程序或适用法律法规错误,[21]重大且明显的违法的情况下订立的行政协议也无效。导致相较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更易导致ppp协议被认定无效。此外,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对行政协议约定的条款进行解释,对协议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人民法院经过审查,根据实际情况,可以作为审查行政协议的依据。[22]即当双方对行政协议解释发生争议的,非当事人的行政机关依据职权作出的解释可能影响法院审查行政协议,而民事诉讼主要由法院对协议争议事项进行解释,与民事诉讼相比,行政诉讼对协议解释的不确定性更高。
三是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情形时,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变更、解除协议的行政行为,且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且合法的,社会资本无法要求撤销行政行为或继续履行,只能请求补偿。与民事诉讼相比,行政诉讼除考虑合同约定外,针对原告提出诉请,还需衡量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资本选择诉讼请求的内容造成限制,但行政机关的行政优益权的行使也需接受人民法院的合法性审查,不存在无限制行使该项权力的情况,[23]且造成相对人损害的,应提供相应的补偿。[24]因此也无需过分担忧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对ppp协议履行的影响。建议在ppp协议中针对此类情形,明确约定予补偿的标准或计算方式,以减少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给社会资本履约造成的不确定性。
四是认定ppp协议为行政协议,影响社会资本选择纠纷解决的方式。根据《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行政协议约定仲裁条款的,除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外,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该条款无效。若认定ppp协议为行政协议的,则无法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纠纷,在现阶段ppp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缺乏直接、明确的判断标准的情况下,建议慎重选择采用仲裁作为争议纠纷的解决方式,应利用《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第七条规定的约定管辖的内容,选择恰当的争议解决法院,为协议双方解决争议奠定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相对于民事诉讼而言,若ppp协议被认定为行政协议,发生纠纷时适用《行政协议案件规定》予以处理时,行政诉讼并无明显优势。当然,提起行政诉讼对社会资本主张实体方面的权利也无实质性影响。但应予注意的是,因行政法律规范对行政机关的限制等因素的影响,若将ppp协议认定为行政协议,并通过行政诉讼解决ppp协议争议,社会资本在履行协议的确定性、寻求救济的方式等方面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影响,通过ppp协议事先约定能够降低部分影响,但并不能完全消除上述限制。
[1] 《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自2018年2月28日起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废止。
[2]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3] 《行政协议案件规定》规定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施行。
[4] 虽然现有规范体系下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特许经营协议的概念有所规定,但显然相关概念的界定并不严谨,包括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与特许经营协议的关系也缺乏唯一确定的观点,主流观点认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与特许经营协议属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适用范围更广。虽然《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第二条将特许经营协议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分别列举,因本文仅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进行论述,为论述方便,除本文特别强调或论述外,将《行政协议案件规定》中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和特许经营协议统称为ppp协议。
[5] 参见耿宝建、殷勤:“行政协议的判定与协议类型案件的审理理念”,载《法律适用》2018年第17期。
[6] 最高人民法院在河南新陵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辉县市人民政府管辖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244号(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9ecdadd739304629b9536414290fceef,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2月11日)中认定:公路建设协议书,系采取bot模式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虽然合同一方当事人为政府,但合同相对方在订立合同及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并不受单方行政行为强制,合同内容包括了具体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体现了当事人的平等、等价协商一致的合意,应按照民事诉讼案件处理。在漳浦中环天川环保水务有限公司与漳浦县环境保护局、漳浦县赤湖镇人民政府等侵权责任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013号(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2bed4328d20f4efab1000878e7317986,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2月11日)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案涉合同为特许经营协议,但未直接依据有名合同及《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直接认定属于行政协议,而是对案涉协议进行认定分析后确认其为行政协议,应按照行政诉讼案件处理。其他关于是否属于行政协议的论述可参考(2018)最高法行申6335号、(2016)最高法行申4236号等案例。
[7] 参见沈福俊:“司法解释中行政协议定义论析—以改造‘法定职责范围内’的表述为中心”,《法学》2017年第10期。
[8] 参见葛琪、李刚:“行政协议判定标准之完善—以最高人民法院403件行政协议案件的分析为切入点”,《人民司法(应用)》,2019.25。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新闻发布会(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0757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2月11日)。另参见四川省大英县人民政府、大英县永佳纸业有限公司乡政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95号(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ea8b6e044a0a4d489e01a87f00b232da,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2月12日)。
[10] 《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履行行政协议过程中,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被告作出变更、解除协议的行政行为后,原告请求撤销该行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行为合法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
[12] 陈天昊:“行政协议的识别与边界”。《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
[14] 同前注8。另参见四川省大英县人民政府、大英县永佳纸业有限公司乡政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95号(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ea8b6e044a0a4d489e01a87f00b232da,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2月12日)。
[15] 参见和田市人民政府与和田市天瑞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兴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2014)民二终字第12号,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6aff23b21d8c471b85b2aa060110c219,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2月11日。
[17]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
[18] 谭红、孔冰冰:“对行政协议纠纷案件受案范围的理解与适用”,《法律适用》,2019年第8期。
[19] 《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第九条:在行政协议案件中,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一)请求判决撤销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二)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或者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三)请求判决确认行政协议的效力;(四)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依法或者按照约定订立行政协议;(五)请求判决撤销、解除行政协议;(六)请求判决行政机关赔偿或者补偿;(七)其他有关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诉讼请求。
[20] 参见蒋大玉与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再审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49号(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063c452fb18942acbc31a89701129f10,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2月12日)。
[21] 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安吉县人民政府其他二审行政判决书(2018)浙行终13号(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505005a23efb4790b567a97c00b1a62a,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2月12日)。
[22] 参见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不予更正土地用途登记案二审行政判决书(2014)萍行终字第10号(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8eeaddd059d74910b5da21fd6b091df6,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2月12日)。
[23] 参见崔龙书与丰县人民政府行政奖励、行政裁决一审行政判决书(2017)苏03行初540号(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901bfdf75d6044b9af3ca8fe00ff5042,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2月12日)。
[24] 参见寿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诉寿光市人民政府、潍坊市人民政府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案(2017)鲁行终191号(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41f27be3884eb6a444fc540436af5d.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2月12日)。